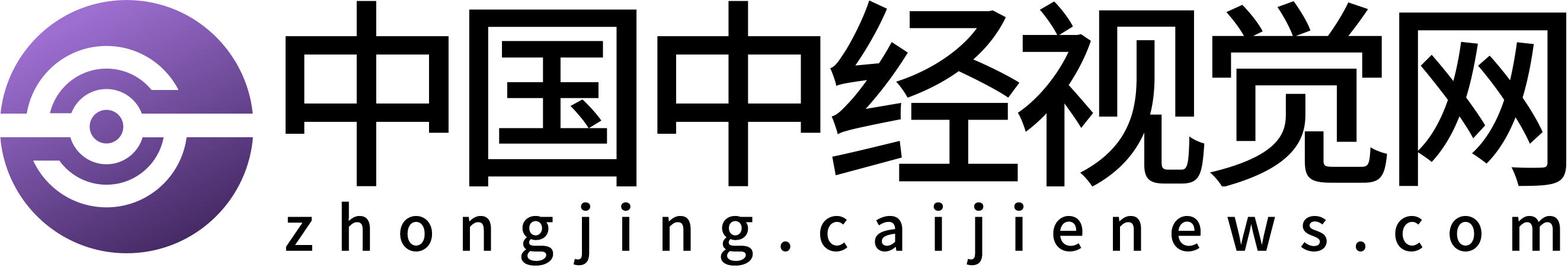割麦记忆
【念念有余】
 (资料图)
(资料图)
麦茬低,收上来的秸秆就多,可以烧火做饭用,用不完的还可以卖给造纸厂,换些钱。
余胜良
我最后一次割麦子是高三那年,我希望自己运镰如飞,希望能三步并做两步,希望自己能带头从地的这头割到那一头,可每次抬头,就发现前面的长辈们离我越来越远,他们挥镰的频率更高,弯腰的时间更长,抬头的次数更少。
金色的麦穗不是浪漫的象征,风吹过来摇曳的样子,不会有人在意,唯一在意的是割麦子的速度,麦芒扎在脖子位置,胳膊慢慢酸痛起来,腰也硬了起来。咳出嗓子里累积的痰液,擤出两个鼻孔的鼻涕,都是黑色的,我对它们的颜色有点惊讶,也有点害怕。远远看上去干净的麦田,等一手抓住它们的颈部,一手握镰从根部割断时,积累几个月的灰尘,会荡到我们眼前,鼻孔里,或者肺里。
麦茬不能太高,镰刀要贴着地,像拉锯一样往怀里拉,身体的重心要放低,善割者不仅要快,割过的麦子码得要齐,还要麦茬矮而平整。麦茬低,是为了种下一季庄稼方便,夏种不需要翻耕,可以在麦茬中间点玉米,压红薯苗,播种大豆。
麦茬低,收上来的秸秆就多,可以烧火做饭用,用不完的还可以卖给造纸厂,换些钱。传统农业时代,光合作用的任何产物都不会浪费,都是紧要的生存资源,可即使这样还是家徒四壁。
我十岁左右,和父亲到他城里的朋友家里走动,他在工厂上班,收入颇丰,当说到割麦子这个话题时,女主人用普通话说,她曾经当知青下乡,割麦子第一下就伤到了脚,等脚养好后,割麦子也就结束了,所以自己没有割过麦子,“非常遗憾”。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遗憾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距离我的语言环境太远,后来想她可能是想掌握一个技能,增加一次尝试。但我觉得并不值得遗憾。
我在她家里,第一次喝到红葡萄酒,吃到哈尔滨红肠,看到大彩电,听他们讨论当时流行的电视剧《人生》,探讨高加林到城市之后如何选择。这一切都离割麦子的生活太遥远,像是两个平行世界的意外触碰。
我们农民的孩子,五六岁就要劳动了,跟在父母后面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等手上的力量强一些,就想学父母的模样,做一些大人才能做的工作,想证明自己有能力,也想分担父母压力。
小孩子喊累的时候,父母习惯性地说小孩子没有腰。其实小孩子腰也会不舒服,很多劳动要用到这个部位,不过没有大人那么疼痛,大人经年劳累,要长久保持一个姿势,会有很多疾病。这些疾病是人类从事农业劳动后,才会有的。
割麦子一年只有一次,是不得不逾越的障碍,好在一年只有一次,后来我看到陕西有职业麦客,深感他们更不容易。
后来看一本书上介绍,人类培育了农作物,借助农作物扩大了人口,产生了各种文明,但同时,这些农作物,也借助人类之手,实现了自身的推广,如果不是人类,他们不可实现如此大的播种范围。这些农作物大多数比较脆弱,竞争不过野草,会遭遇病虫害,都有赖于人类帮忙。为了收获,农民要忍受枯燥和单调的重复,日复一日。
麦子从麦糠里脱离后,抓在手上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颗粒匀称漂亮,晾到场上接受阳光的再次关照,灌装时,会感觉麦子比我们的身体还要干净,等到装在麦屯里,人们的心情终于放松下来,有这些麦子垫底,这一年就饿不死人了。人们忘记艰苦的劳动,麦子是这样的让人舒服。
那一年割完村南地块的麦子,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带着父母对我脱离农业劳动的期待,备战高考,和千万农村学子一样。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