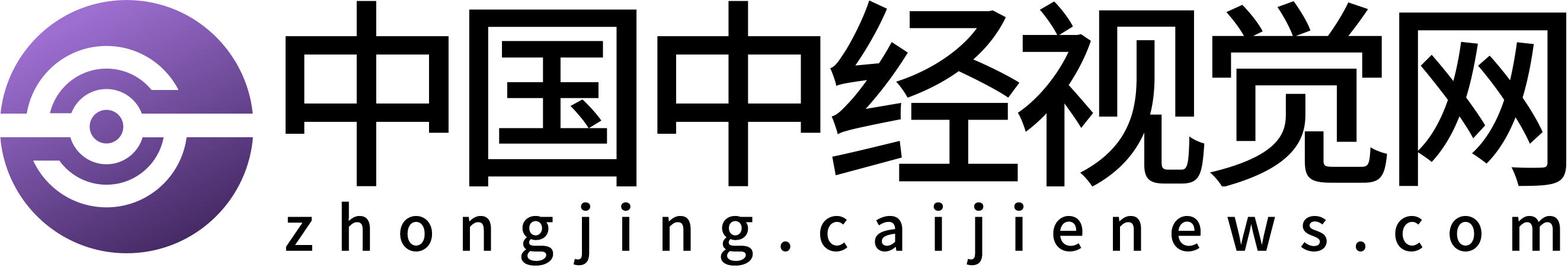五十年后再相会
1968年12月,我作为一名知青,插队落户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泥塘村。2018年秋,恰值下乡插队50周年,我与当时的队友们相约回到泥塘村,拜望父老乡亲们。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们出发之前,合肥四中的部分老知青已组团前往当年的下放地宿松县程营公社探访,当地的一位老人骑摩托车为大巴车带路到泥塘村。众人上车时,这位带路的老人忽开言道:“哈晓斯怎么没来?你们谁认得他,请带个信,就说我姓徐!”此言说得突兀,听的人也颇为讶异。这番话被发到同学群中,有人猜测这个老徐与我曾有过什么约定。
其时,我正为几天后的返乡之行筹划方案,苦于与乡亲们失联多年,对泥塘村的近况一无所知。听闻此消息,我喜出望外,这至少说明泥塘村还有人记得我。
那几天,我四处打听老徐的联系方式,终于有同学从邻村一位老乡那里打听到了他的手机号码。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拨通老徐的电话,并报出自己的名字,电话那头,老徐“嘿嘿”地笑着。得知我们一行人要回泥塘村,老徐连声说好,并大致说了一些老友的近况:梅会计还在村里,记分员王金狗前些年去世了,王队长还在,已经80多岁了……
几分钟后,有位老乡打来视频电话,他操着浓重的宿松口音大声嚷道:“我是小木匠啊!”这一声,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50年前。那时候,田要集体种,坝要集体挑,在村里能单枪匹马干活挣钱的,就数走村串乡的小木匠和他的哥哥大木匠了。小木匠与我年龄相仿,那时候,逢晚间下工或者没活儿做时,他总爱到我这里聊天。小木匠问到泥塘之行的安排,我说想在村里住一晚,希望能找个场地和乡亲们搞一场联欢会。小木匠听罢,朗声笑道:“你们8个人全住在我家,场地就设在我家!”
那一天,我们的车辆驶入汇口镇泥塘村。汇口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码头,也是当年下乡时我们卖棉花的目的地。记得那时赶着牛车到汇口卖棉花,单程得花两个小时,如今开车用不了20分钟。老乡们特地带我们从江堤上走,岸柳婆娑,秋水浩瀚,遥想当年,挑土护堤是知青们每年冬季最为艰苦的挑战。寒冬腊月,挑着铺盖上堤,吃住都在堤上,一干就是一个多月。公社按人头分配土方任务,挑完土还需夯实,各队展开劳动竞赛,队长们铆着劲鼓动大伙拼命干。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一直干到夜幕落下才收工。
我努力追寻早年的记忆,原先的土坯房早已不复存在,独门独栋的两层楼房沿村道一字排列。老徐介绍说,原先的泥塘大队如今划分成了若干村民组,并与原张月和排湾两个大队合并为张月行政村。
在老乡们的导引下,我们来到小木匠家。只见院门上方高悬红底黄字横幅“泥塘人民欢迎老知青光临第二故乡”,有乡亲在一旁点燃了鞭炮。在热烈的欢迎仪式中,望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我心中百感交集。
梅会计、老徐、小木匠等人领着我去探望当年的老乡亲,80多岁的王队长正在家中干活,他握住我的手却认不出,一旁的小木匠赶紧提醒,老队长连声喊着我的名字……沿着几十米长的村道走下来,见了十几位乡亲,有些当年还是小孩子,一放学就到我屋里玩,现在还能清晰地讲述当年的故事。
晚宴安排在小木匠家,灶上自下午就忙活起来。乡间佳肴,久违的味道,令人未饮已醉。
宴席散去,联欢晚会开始。张月村支书首先致辞,对老知青们回到第二故乡表示欢迎。随后,我代表老知青们对当年的插队经历做了简单概括,并向泥塘村的父老乡亲们致谢。开场节目是泥塘村乡亲表演的黄梅戏小段,声正腔圆,赢得阵阵掌声。接下来,黄梅戏对唱、双人舞、太极操表演……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把晚会推向高潮。联欢会一直延续到夜深,散场时,大家都有些不舍。
次日早饭后,我们向乡亲们道别。我说以后还会再来,小木匠握住我的手说,这么多年才来一次,以后哪会再来呢?
我们与泥塘村乡亲们的感情是炙热淳朴的,此生定能相互铭记。因缘际会,惺惺相惜。回望青春,亦苦亦甜。
标签: